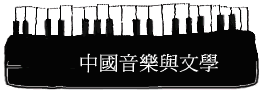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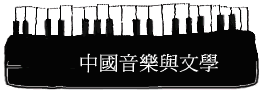
「音樂是經過耳朵的浪漫詩」
從中國『詩經』的先民詩歌、古希臘『奧德賽』的敘事史詩,東西方古典詩詞結合詩與樂的音韻傳統,文學與音樂,自古便不斷轉換著形式相互襯映。近代則更顏密互動,展開歌劇、藝術歌曲、標題旋律的創造衍生,更豐富文學的感性內涵。

|
|
<<詩經>> <詩經>為中國最古老的樂歌集,收錄西周至春秋時代共305篇可配樂歌唱的詩歌。內容可分為風<民歌謠曲>、雅<宮廷樂歌>、頌<祭祀樂歌>三部份,以琴、瑟等樂器伴奏歌唱。當時樂譜已經失傳,流傳至今的歌詞,一般是結構和韻律整齊的四言詩。在詩為音樂可教化人心的春秋時代,不但廣泛應用於政治、社交儀式之中,並作為教育貴族子弟的音樂教材。 |
|
『高山』、『流水』 伯牙巧遇知音鍾子期、出自「呂氏春秋」及「列子」記載,是中國廣為流傳關於「知音」的描繪代表。春秋時代樂師伯牙,精通琴樂演奏。「荀子」:「伯牙鼓琴,而六馬仰秣」,其精妙的琴聲連正在吃草的駿馬也會停下來仰頭聆聽。伯牙繪山寓水的琴曲「高山」、「流水」,僅以樂聲讓鍾子期深深體會,曰:「巍巍乎若泰山」、「湯湯乎若流水」。因此「鍾子期死,伯牙破琴絕弦,終身不竹鼓琴,….」 |
|
|
鳳首箜篌 |
『李憑箜篌引』 「李憑箜篌引」是唐代詩人李賀描繪長安樂師李憑彈奏箜篌之作。整首詩作全是以聽覺寫聲音,更加入各種知覺及想像。像是「昆山玉碎鳳凰叫,芙蓉泣露香蘭笑。」前者以聲喻聲,描繪清脆及嘹亮的樂聲,後者以形喻聲,分別抒寫曲調的悲傷與歡悅。而「女媧練石補天地,石破天逗秋雨」則更進一步以境喻聲,樂音不但讓女媧忘了補石,箜篌聲震破天際,秋雨也淅瀝降到人間,在在均傳達李憑演奏的神妙境界。
|
|
「琵琶行」 「琵琶行」是描繪琵琶 音樂之經典敘事長詩。乃唐代詩人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期間,某夜於潯陽江邊聽到琵琶聲,循聲訪人,找到昔為長安歌女的琵琶主人。琵琶女應邀移船相見,為眾人演奏並述身世。詩人心有所感,,而成「琵琶行」。詩文運用中文語言文字上的特質,產生近似音樂的效果,其中「大絃嘈嘈如急雨,小絃切切如私語;嘈嘈切切錯雜彈,大珠小珠落玉盤」四句,成為今日描繪樂音的經典佳句,展現中文「詩樂一體」的情境。 |
|
|
|
「紅樓夢」裡榮寧二府、大觀園裡上上下下,真正懂得欣賞音樂的要屬賈母史太君了。她平日喜歡熱鬧,看戲也愛熱鬧,聽音樂則喜歡笛子獨奏,往往在月白風清之時,令演奏者遠遠隔著池水,吹奏那抒情、深沈的曲調。 「只見一個婆子走來,請問賈母說:『姑娘們都到了藉香園,請示下:就演吧,還是再等一會兒呢?』…..不一時,只聽得簫管悠揚,笙笛並發;正值風清氣爽之時,那樂聲穿林渡水而來,自然使人神怡心曠」-「紅樓夢」第四十一回 |
『老殘遊記』
「明湖居聽書」出自「老殘遊記」第二回之後半,敘述老殘經歷一場「說鼓書」的情形。不同於以古體詩寫成的「琵琶行」,劉鶚的「明湖居聽書」並非韻文,但同樣是中國文學作品中以文述樂的代表作。在描述白妞王小玉的說唱藝術時,作者不僅運用了類似白居易的聲詞與隱喻手法,且進一步鎔鑄新詞,更具體地以演出當地之名勝泰山以及險奇黃山的竹虱景,來指涉聲音的層層壘起變化,文字運用之妙,可說更勝前人。
「王小玉便啟朱脣,發皓齒,唱了幾句書兒。聲音初不甚大,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。五臟六腑裡,像熨斗燙過,無一處不伏貼;三萬六千個毛孔,像吃了人蔘果,無一個毛孔不暢快」-「老殘遊記」『明湖居聽書』